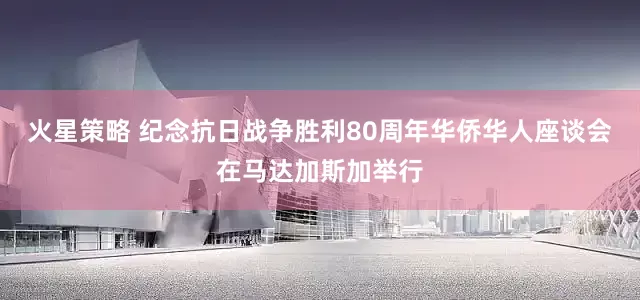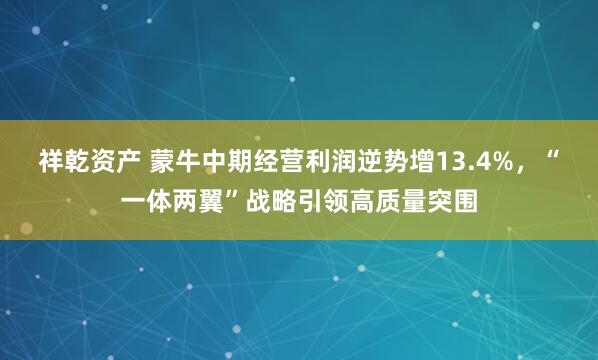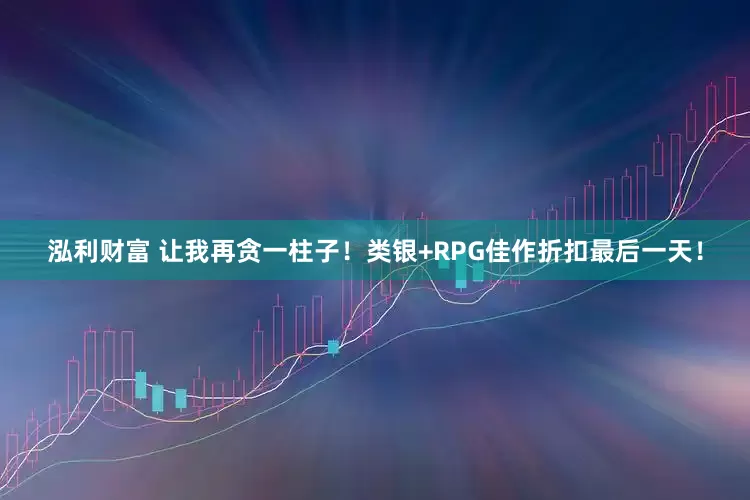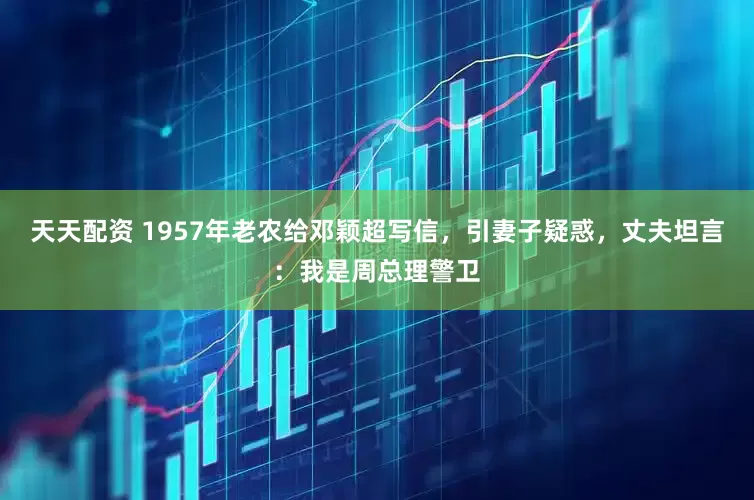
“1957年10月的一个深夜,何明德点着油灯天天配资,小声对妻子说:‘信一定要写给邓大姐,北京她最认得我。’”
妻子听得一头雾水——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,为何偏偏要给全国闻名的邓颖超写信?何明德却只是抿嘴一笑,把薄薄几页纸折好,揣进棉衣内袋。第二天一早,他步行二十里路到县城,把信投进绿色邮筒。信封上,落款“原红四方面军何明德”。这奇怪的举动,很快在乡里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信走了十来天,先送到国务院办公厅,再转到中南海西花厅。邓颖超拆开信,只看了“警卫员小何”几个字,立刻对秘书说:“原来他还在!我和总理一直以为这孩子牺牲了。”当天傍晚,她提笔写下一张证明,盖章后回寄四川通江县。北京的秋风里,这封写着“同志仍在”的信,带着久别的温度南下。
可在川北山坳的小院里,妻子依旧半信半疑。她认得丈夫能吃苦,会木工,也会修农具,却难以把他与“首长警卫”四个字联系起来。何明德见她摇头,干脆把尘封十五年的往事一股脑儿说出:“我真跟周总理混过,枪法还行,当年腰里插两把勃朗宁哩!”
时间拨回二十四年前。1933年春天天天配资,15岁的何明德揣着一口粗茶淡饭的倔劲儿,跟着红四方面军翻山越岭。那年,他脚底磨出血泡,也没掉队——因为他听小商贩讲过“革命能让穷人翻身”。饿着肚子走夜路,他对自己说:只要活下去,总有机会替穷人撑腰。
三年后,西安的寒风里,机会来了。1936年12月中旬,他被临时抽调到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。第一次见到周总理,他愣是没敢抬头。周总理却拍拍他肩膀:“小何,别紧张,跟我时间长了就习惯。”一句话,让他憋着的那口气一下松了。

真正考验在1937年4月的劳山伏击。周恩来一行乘卡车下山,突然枪声四起,尘土飞扬。司机中弹,汽车冲进路沟。周恩来低声命令:“散开,还击!”何明德滚下车,一手短枪,一手攥着周总理的衣袖,硬是护着首长从弹雨里钻向荒草坡。事后他常感叹:“那天要是慢半拍,咱俩都交代在沟里了。”
紧张日子一件接一件。1938年,他们转往武汉做统战。周总理忙着会见李宗仁、冯玉祥,合纵连横;间隙里却关心小何的婚事:“组织会给你介绍文化人,你自己也得多念书。”何明德红着脸答“是”。他说后来自己能认得报纸,就是那阵子被总理逼着学拼音字母。
转折发生在1942年。周总理去延安办公前,准许他回老家探亲一个月。“路上若有急事,来信!”临别嘱托还在耳边,意外却先降临。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这个突然返乡的壮汉,先抓父亲,又日夜监视。为了救爹,他典了房子,掏空家底,才换得自由。可代价是无法再返回延安。写信求援?一落笔就可能连累全家。思前想后天天配资,他决定“先苟住”。这“苟”就是五年。

1949年,解放军进驻通江。乡亲们夹道欢迎,何明德望着新四军番号,喃喃一句:“自己人终于回来了。”他跟老婆提起往昔,她当玩笑听。他也懒得辩,白天带民兵练枪,晚上帮公社记工分,就这样过到1957年。
组织关系却一直是他的心病。县里摸底党员,他报了名,没有人能够核实。一连几年,他像被丢失的档案,既不是“假党员”,也不是“真党员”。拖到那年秋天,他咬咬牙,给北京写信。信不长,寥寥几页,却列举了当年西安、武汉时周边同志的姓名职务,末尾只写一句:“愿以生命担保,字字属实。”
邓颖超的回信到达那天,通江邮差一路小跑,边跑边喊:“何明德,大首长来信啦!”妻子捧着信封,认得那醒目的钢笔字:邓颖超。她再看丈夫,眼里多了三分敬重。几个月后,县委正式为他恢复党员身份,还想大张旗鼓宣传。何明德摆手:“别折腾,地里庄稼还等着收呢。”他把邓颖超的证明夹在《新华字典》里,锁进木箱,只在过年时拿出来擦擦灰。
有人问他,失去十几年组织关系,值吗?他想了想,说:“保住一家老小,也保住了咱党的秘密,值!”话音不高,却掷地有声。

晚年,他依旧早起种地、晚来读报。偶尔有村干部请他讲“西安事变”“劳山脱险”,他总先冲大家摆手:“不是我能耐大,是总理指挥得好。”说罢便哈哈大笑,皱纹里全是踏实的光亮。不得不说,这样的荣光,比镁光灯下的掌声更耐人寻味。
邓颖超后来提起“小何”,常感慨一句:“忠诚的人,从不需要太多言语。”一句话,说尽那封信的分量,也说尽一个老警卫员的坚守。
广瑞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